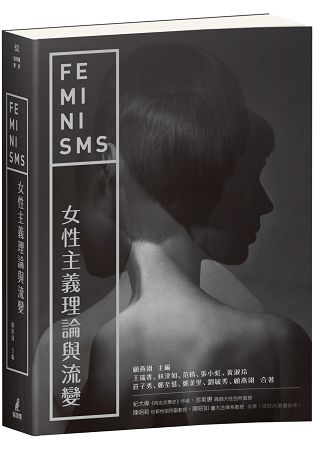
女性主義理論與流變(FEMINISMS)
顧燕翎主編(Yenlin Ku, chief editor)
貓頭鷹出版社 2019年1月30日
顧燕翎主編(Yenlin Ku, chief editor)
貓頭鷹出版社 2019年1月30日
導言
顧燕翎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一日亞洲時區中午十一點開始,Google全球分公司的員工陸續放下手邊工作,走出辦公室抗議公司沒有認真處理性騷擾案件。Google的罷工和近年席捲全球的#MeToo一樣,都不是單一或突發的行動,而是自十九世紀以來婦女運動的一環。婦運原就具有全球串連的特質,到了網路便捷的二十一世紀,發言管道更為暢通,蓄積己久的能量便勢如燎原。
拒絕性騷擾和性侵害,是第二波婦運後期激進女性主義者的主張。之前男人侵犯女人,被視為男人與生俱來、以及男人之間互相交換的權利/力,被侵犯的女人反因害怕名聲受損而不敢聲張。#MeToo在歐美地區的巨大爆發力,反映了當地女性主義所創造的新價值已累積了深厚能量,讓受害者風險降低,也使更多旁觀者敢於不畏權勢,公開出面譴責加害者。亞洲的婦運相對沉默,韓國高階檢察官徐智賢公開陳述自己被性騷擾又被降職的過程是極為少數的特例。
臺灣的婦運自一九八〇年代以來已有許多法律和制度建樹,深入政府體制,表面上聲勢盛大,但在#MeToo的考驗中卻失去了聲量。部分受害者即使已不再躲藏,尋求專業協助,卻選擇隱姓埋名,以免再受傷害。她們仍處於孤軍奮戰的局面,厭女[1]的社會價值尚有待解構。女性主義在父權陰影下匍匐向前,其路徑從來不是直缐的。
本書初版《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完成於一九九六年,當時女性主義已由社會禁忌蛻變為顯學和流行語,為了幫助人們認識女性主義的歷史、內涵和意義,我利用多年來整理的教案,透過任教的交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申請到教育部補助款,邀集作者們就女性主義的理論和歷史源流做一全面的整理探討,完成了全球第一本以中文書寫的女性主義理論書籍,交由成立未久的女書店出版發行。當年即得到聯合報年度十大好書獎,也受到各地華文讀者的喜愛,成為女書店的「鎮店之寶」。
本書兩千年再版時做了小部分增添修改。事隔近二十年,婦女運動又挖掘了更多史料,生產了更多文獻,女性主義各流派間也相互跨越、影響,而產生了不少變化,所以從去年開始,再進行不同幅度的修改或重寫。書名也改為《女性主義理論與流變》,商請發行中文版《第二性》的貓頭鷹出版社發行。
「女性主義」一詞起源於十九世紀法國,意指挑戰男尊女卑傳統的婦女運動,因離經叛道,長期受主流社會冷眼相待,直到二十世紀後期才得以翻轉,受到較正面評價,而將中止女性的附屬地位或者建立女性主體性的種種作為統稱做女性主義。美國暢銷作家和大學教授羅珊蓋伊(Roxane Gay)在她的文集《不合格女性主義者》(Bad Feminist: Essays, 2014)中表示,她曾抗拒女性主義,但當她了解女性主義在所有領域提倡性別平等,並且也考慮左右每個人變成什麼樣的人、做什麼樣的事的所有因素的時候,就容易接受女性主義了。(她本人是海地第二代移民,身材肥胖,少年時曾受同學輪暴但不敢聲張,有過一段漂泊的人生。)「女性主義帶給我平和,引導我如何寫作、如何閱讀、如何生活。我有時候會出軌,但我知道沒有做到最好也沒有關係。」
女性主義和婦女運動皆肇因於人們主觀上感受到男女不平等,或女性受到壓迫,而謀求改變現狀。女性主義發展理論,婦女運動實踐、檢驗和修正理論,理論與行動相輔相成,所以許多女性主義者也同時積極參與婦運。婦運發生前,社會上不平等或女性受壓迫的客觀現象就已存在(如溺女嬰、鬻女、毆妻等史實),但若非改變現狀的社會條件已經成熟(例如,女性受教育、中產階級興起、政治民主化),而且有足夠數目的女性主觀上不願意再忍受壓迫,婦運不可能發生。換個角度來看,當了解到女性的次等地位是人為的、被社會建構的,而非天生的、自然的,才可能以人的力量來扭轉。所謂女性主義理論便是在:一、分析男女不平等的現象,或女性的次等處境。二、以女性觀點解釋其原因。非女性主義學者雖也曾注意到兩性社會處境和心理狀態之異,但他們往往以生物決定論,也就是女性先天有缺陷,或者以交換理論來解釋,指女性為了延續種族而自願放棄自主性,以換取男性的保護與供給,最終得到女性地位無法改變或不需改變的結論。女性主義者著重於社會文化因素,使得改革顯得不僅可能,而且可欲。三、尋求改變。不同流派的女性主義者根據各自對人性與社會的理解,與對理想社會的想像,提出漸近式改革或革命性變革的方案,以達到男女平等、女性解放或建立新文化、新倫理的目標。整體而言,女性主義可說是解構父權體制、建立新文化的思想工具與行動方案。
女性的處境有著跨越時空的共同性,也有其內部的相異性。女性主義理論受到主流思潮衝擊,在不同時代、地域、文化情境下,各自對婦女的次等地位做出詮釋,並提出解方。早期的女性主義,其推衍發展的脈絡清晰分明。近數十年來,社會文化和婦女處境快速變遷,女性主義理論也隨之修正,加以各流派交互批判、啟發、混合,而發展出新的樣貌。例如,標榜體制內改革的自由主義女性主義團體,吸收了年輕、激進的成員後,修改其原有路線,在策略和理念上變得更為激進;有些激進小團體為了發展庇護所等服務所需的資源,與體制稍做妥協;也有激進女性主義者走上女同志的分離主義路線;或成為生態女性主義者,企圖恢復她們被男權「馴化」前精力充沛的野性。在爬梳女性歷史時,我驚覺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女性主義前輩,竟然時有比當代女性更為激進的言論。
各流派女性主義固然各有特色,但因其目的都是批判改造父權文化,所以也不乏重疊神似之處。當我們研究個別女性主義者的主張時,常感到難以斷然區分。此外,個人思想除了可能與時推移,在個別議題上也可能受到不同流派的召喚,而做出相應的選擇,並不固守流派。不過,為求對女性主義有較為結構性、脈絡性的了解,流派的分類仍是被廣為採用的方法。只是因取材重點不同,各書對流派有不同命名和歸類方法。本書參考國內外慣例,按照歷史進程及特質將女性主義劃分為十一類: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存在主義女性主義、激進女性主義、精神分析女性主義、女同志理論、生態女性主義、後現代女性主義、國家女性主義及後殖民女性主義。與舊版相較,增加了晚近盛行的國家女性主義。每一類分別以單章處理,由一至兩位作者負責介紹各流派的社會背景、思想源流、重要主張及檢討,並且儘量關照到當下的實踐。其中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分為兩章處理。
自由主義女性主義
自由(個人)主義女性主義在時間上是所有女性主義的起點,在理論上也成為之後其他各流派的出發點,或批判改造的對象。十八世紀歐洲啟蒙時代,受過教育的女性,被新資產階級男人反抗君權所啟發,在私人生活中質疑男權的神聖性,要求與男性平等的權利和個人自由。新生的自由主義崇尚理性,主張人之異於禽類是因其具有推理能力,而非徒具人之形體,所有的人在接受教育後都具備同等的理性,故應平等相待。個人基於理性,能為自己做最好的決定,追求自我的利益,所以應享有充分的自主權。個人意志不從屬於他人(如君王),個人自由亦不應受他人干涉;國家對個人保持中立無偏的態度,保障人人享有平等機會,以及個人的人身安全、財產和自由;國家的權力只在公領域運作,不應涉入私領域。只是他們論述中的個人,往往僅限於特定種族(白人)、階級(有產者)、性別(男性),女人被視為男人的附屬品,而非平等的公民。男性思想家被習俗賦予的性別優勢,終究成為其難以破除的性別盲點。
十八世紀英國的吳爾史東(Mary
wollstonecraft1759-1797)首先在《女權辯護論》(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1792)一書中,將自由主義的理念推及至女性,強調女人與男人無異,皆具有理性思辨能力,是習俗和兩性差別教育造成了男女不平等。為消弭人為的不平等,女性應獲得同質的教育,在人格和經濟上獨立自主。十九世紀英國的約翰.米爾(John Mill 1806-1873)和其妻海莉.泰勒(Harriet Taylor 1807-1858)主張,人除了衣食,最大的需求是自由,有自由才有尊嚴,才能感到人的價值。男女任何一方受到壓抑,都會阻礙人類進步,違反其主張的功利(utilitarian)自由主義乃是追求最大多數人最大幸福的原則。米爾首先在英國國會主張婦女投票權、全民義務教育和民意代表的比例代表制。同時代的美國婦運除了爭取女性投票、公開演講和參與公共事務的權利,婦運領袖史坦登(Elizabeth Cady Stanton 1815-1902)更主張實質平等,應尊重性別經驗的差異性。曾為黑奴的婦運者特魯思(Sojourner Truth c. 1797-1883)更以其自身遭遇,指出種族和性別的多重歧視。一九六三年傅利丹(Betty
Friedan 1921-2006)藉《女性迷思》說出美國中產女性困居家庭的苦惱,一九六六年組成「全國婦女組織」(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 NOW),「帶領婦女全面加入美國社會主流,與男性以完全平等的伙伴關係行使所有權利。」一九七〇和八〇年代,臺灣的婦女運動受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的影響,如「先做人,再做男人或女人」、「人盡其才」、反對婦女保障名額、修改法律中的性別歧視等主張,都展現追求與男性平等的精神。
二十世紀後期,自由主義女性主義受到激進女性主義啟發,開始重視個人的多元差異和交叉位置,主張擴大公領域的範圍,提升國家照顧弱勢的責任和權力,例如家暴受害者。同時,有鑒於個人自我實現的機會深受經濟影響,也注重分配的公平性,倡議以補償性的制度,強化實質平等;在法律方面,則由修改性別歧視的法律,轉而以立法積極消除歧視、矯正不平等。早期的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者鼓吹公領域對女性開放,卻未論及私領域的分工重組。一九八〇年代後,終於體認到齊家治國一肩雙挑之不易,而提出家務分工、彈性工時及減輕男性養家重擔等主張。其他女性主義者往往批評她們承襲了自由主義的盲點,如:一、過分崇尚男性價值,重視心智勝於情感與身體;二、強調個人先於社會,區分公私領域;三、注重抽象的、形式的平等,未顧及性別內部差異。然而,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者的性別身體和性別經驗與男性自由主義者有別,現實的落差必然會發展出不同的性別視野。自十九世紀起,她們除了主張開發女性的智能,也非常重視鍛鍊體魄,視其為女性獨立自主的必要條件;二十世紀後,更要求公權力介入改善弱勢者的生存條件,和私領域內的權力關係,以保障個人的自由選擇權;到了二十世紀後期,考慮到性別之內的種族、階級、年齡、性傾向等差異,主張國家應負起消除所有形式歧視的責任。
烏托邦社會主義女性主義/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
十九世紀的工業革命和法國大革命,使人類歷史產生了驚天動地的變化,也促生了平等、互愛、共享的社會主義思想。早期的社會主義女性主義思想的代表人物為德國的比柏(August Bebel 1840-1913)、美國的紀爾曼 (
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1860-1935)、俄國的柯崙泰(Alexandra
Kollontai 1872-1952)等,他/她們主張人類社會為一有機整體,互相依存,所以應以合作的集體主義取代自私的個人主義;婦女應從個別的家庭中解放出來,直接參與社會生產工作,成為社會一分子,不再依賴個別男人;婚姻應以個人情慾為基礎,而不再是經濟的、社會的、消費的單位;並且以集體化生活取代私人家庭和家務。
在本書中,黃淑玲以英國歐文社會主義為起點,介紹歐文 (Robert Owen 1771-1858)和湯姆士(William
Thompson 1775-1833)的廢除私產、提倡情愛自由等主張,及其未竟成功的公社實驗。馬克思主義者以為早期的社會主義過於樂觀,譏之為烏托邦,因此在二十世紀初期的中文譯名為「空想社會主義」。馬克思、恩格斯等人以「科學的」分析方法,特別是歷史唯物論(historical materialism),突顯人的生物性和社會性之間的辯證關係,說明人性並非一成不變,而是在特定歷史情境、生產活動中形成的,並且強調階級社會對個人意識形態和日常生活造成的結構性影響,這些觀點都對女性主義者有重要啟發。本章詳細說明馬克思主義中的意識形態、階級意識、異化、實踐等概念,並深入介紹恩格斯的
《家庭、私有財產和國家的起源》一書,及其對女性守貞、處女情結等社會習俗的觀點。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被批評為經濟決定論,同時忽略了女性投入一生精力的再生產活動。不過馬克思對自由的定義︰不僅是個人生活消極的不受干預,而且個人需擁有充分的物質條件方有能力行使其法律權利,仍深切影響了其他派別的女性主義者。
存在主義女性主義
存在主義女性主義和西蒙.波娃可以說是二為一,一為二,本書曾考慮將其併入激進女性主義之章節,但後來決定單獨成立一章。其理由有二:一、《第二性》為女性主義空前巨著,影響深遠;二、向當代女性主義的啟蒙者波娃致敬。
二次大戰後百廢待舉,人們對戰禍感到厭惡、荒謬,存在主義適時於法國興起,重建人們劫後餘生的自信,相信人的努力能使明日世界比今日更好,學習接受現狀,戰勝精神創傷,明日之我也可以超越今日之我。存在主義代表人物沙特主張,個人在本質上是自由獨立的,在追求自由的過程中,他會遭遇其他人,其他人亦有其自我意識,所以人各有主體性。只是在個人的主觀意識中,視其他人為客體,所謂客體是具有已經定型的特質(identity),而非全然自由。只是被定型化的客體並不完全認同被對方設定的性質,他為了保持自己主體的獨立性,永遠企圖超越對方設定的特質去探索新狀況。因此,所有自由主體之間都存有無可避免的敵意,彼此視對方威脅了自己的自由,為了克服威脅,便設法使對方臣服,否定其自由,使之成為一個具有固定特質,相對於自己而存在的客體,也就是他者。
波娃應用這個理論來解釋男女的相對關係:在古早男女的自由之戰中,女人受到身體的拖累(如:懷孕、生育)而失去自主性,變成因男人而存在的他者,臣服於主體的客體。之後一代代的女人都未能固守自己的自由,而自認失敗。因為女人未能克服敗績,而使得失敗顯得難以避免,看不到任何改變的可能。
波娃否認所謂女性特質是天生的。做為一個自由的主體,女人可以定義、創造自己的內涵。然而在她看來,即使第一波婦運締造了制度性的改變,例如女性取得投票權、受教權、財產權等,仍未能獲得充分自由。婦運者所創造的改變只不過是象徵性的騷動,她們得到的只是男人願意給的,因而仍處於被動的客體位置,被動地接受男人對她們的定義。波娃激進地主張,女人應當拒絕傳統女性角色,自由獨立生活,她自己便選擇不結婚,也不生育子女,但卻被批評過於認同男性價值,以及對婦女的真實處境和歷史了解不足。
在《第二性》一書結尾,波娃曾表明自己不是女性主義者,因她相信社會主義將解決婦女問題。一九七〇年代以後,波娃體會到,婦女需要主動改變自己的命運,不能完全依賴社會的改變,於是積極投入婦運,在法國墮胎尚未合法化的年代,她公開承認自己有墮胎經驗,並且出借住所供年輕女性墮胎。她肯定女性集體行動的力量,也更正面看待女人的身體。
在本章中,鄭至慧扼要介紹《第二性》的要點、存在主義的時代背景、思想脈絡以及重要概念,如意識、自我、無有、壞信念、他者等,並在此基礎上,闡釋波娃如何分析女人的命運、經驗及有關女人的神話,並且回應後人對波娃的批判。
激進女性主義
激進女性主義於一九六〇年代末誕生於美國,是女性主義所有派別中最極端的形式,也是婦女解放運動的論述基礎。受到共產革命的啟發,年輕的左派女性最初自稱激進分子(radicals),並不認同女性主義,反而稱婦運人士為反革命的改革派。費爾史東(Shulamith Firestone
1945-2012)首先改變立場,認可早年第一波婦女運動,指出婦運有其激進的歷史,只是因政治因素而被埋沒。這些年輕女性於是自稱激進女性主義者(radical feminists),一方面連結十九世紀婦運的feminists,一方面彰顯革命的激進立場,以示與改革立場有所區隔。
激進女性主義主張,女人所受的壓迫是最根本、最深刻的剝削形式,且是一切壓迫的基礎,原因如下:一、產生的時間最早,早到個人出生之前,早到家庭制度形成之初;二、流傳最廣,父權體制在當今社會無所不在;三、即使消除了階級,內化的父權價值仍繼續壓迫女性,這現象在過去的共產國家可得印證;四、因為最深、最廣,所以引起受害者質、量方面最大的痛苦,但壓迫者及受害者卻可能習焉不察;五、對女性受壓迫的了解,有助於了解其他形式的壓迫。縱觀歷史,幾乎所有的權力結構都由男性支配,以暴力為後盾。男性間雖也有權力落差,少數男人統治其他男人,但所有男性皆受惠於男性至上和女性受剝削的果實。激進女性主義者不信任男性控制的權力結構,無意在此結構內爭取平等,也不發展全國性組織,而是採取體制外路線,進行體制外抗爭,目標為根本改造社會。
麥金能(Catharine Mackinnon 1946-)曾表示,自由主義女性主義是自由主義應用於女性,社會主義女性主義是社會主義應用於女性,只有激進女性主義才是原生的女性主義,也是女性主義的原型,由此衍生其他派別,如女同志、精神分析、生態等女性主義。激進女性主義不套用已定型的社會理論,首先提出女性觀點的社會分析,解析父權體制、解構性別、大膽質疑文化常模,探究和實驗新的可能性,往往先實踐再建立理論,雖富有創造性,但較缺乏體系。
全新的女性觀點是激進女性主義對女性主義最大的貢獻,「個人的即政治的」翻轉了自由主義的公私之別,將隱藏於私領域、從未受到質疑、男駕馭女的權力關係攤在陽光下,變成可公共討論的政治議題。激進女性主義點出,個別女性在私領域遭受的不幸有其共同性,這些共同性指向社會結構性的問題,開創了社會議題新的、性別角度的分析面向。「性政治」重新定義「政治」,政治不是指選舉,而是人與人之間的權力關係,性政治則是個別男人支配個別女人的權力關係。激進女性主義特別洞察父權社會中公私內外之別,指出以男性為主的「公領域」實則建立在女人無償、片面的勞務付出之上,也就是說,女人在家庭內外的照顧者角色,使得公領域男性無後顧之憂,因而造就了公領域。而公領域的權力和價值也早已透過法律和習俗,進入私人生活和個人心態,成為內化的價值,需要深入剖析,方能見其運作。激進女性主義基本上否定生理功能以外的性別分類,主張人有個別差異,但不應有性別角色之分,社會上存在的性別差異是由男性群體為自己的利益所創,對女性不利,因此女性應努力去除或超越這個分類。或是做個陰陽同體的完整的人,順其自然,破除人為的陰陽特質二分和對立;或者是不與男性牽連,採取不同程度的分離主義,最徹底的方式是成為女同性戀者。退出父權體制、建立新社會的立場,被部分社會主義和性解放女性主義者詮釋為放棄和父權的鬥爭,擁抱女性特質,因而稱之為文化女性主義。不過被點名為文化女性主義者無人接受此標籤,也根本上不同意以本質論取代社會建構論。
取回身體自主權是激進女性主義的重要主張,父權社會使用暴力逼迫婦女就範,控制女人的性、生育和勞務。強暴不是一時興起、個人對個人的暴力行動,而是掌權階級成員對付無權者的政治迫害,讓女人因害怕而屈從或不得不接受保護,加害者與保護者都是男性,兩者有一種共謀關係。性侵害和性騷擾非僅是暴力或性慾發洩,更是性別歧視,應當從女性,尤其是受害者的觀點來界定。
精神分析女性主義
佛洛伊德是厭女症的代表性人物,和同時代的大部分男性一樣,他接受傳統的性別偏見,反對婦女運動,不關心、也不了解女性的處境。他的理論,如伊底帕斯情結、閹割恐懼、陽具歆羨,都是以男性經驗和男性身體為常模,套用在女性身上,據此指出女性的不足和自卑。他過於強調男女身體的外表差異,完全忽略社會因素對心理的影響,受到自波娃以來不同流派女性主義者的批判,包括米列、費爾史東、傅利丹等人,全部指向佛洛伊德以精神分析理論將父權價值正當化,混淆生物與文化,加強傳統男女角色的定型化。
不過,另一些女性主義者則正面使用佛洛依德的理論,將眼光放在嬰兒期生活經驗,分析社會性別常模如何加諸於嬰兒,如何建構人類心理。例如,研究母職(motherhood)和人格發展關係的丁尼思坦(Dorothy Dinnerstein 1923-1992),看到母親(女性)獨自擔當育幼工作,成為嬰兒生活資源的唯一來源和愛恨情結投射的唯一對象,而主張以男女共同育兒來化解對單一性別(母親)的敵意。喬得羅(Nancy Chodorow)則以客體關係理論(object relations theory)來改寫佛洛伊德的社會性別認同的概念。幼兒持續依戀母親,不是生物的必然,而是因為嬰兒由母親單獨照顧。為了避免歧視,並且提升女性的自我意識,她也主張雙親共同育兒,並且應提升女性的社經地位。米契爾(Juliet Mitchell)主張,佛氏的理論經過拉岡去除其中的生物決定論後,可被女性主義用來建構性別主體,讓人們看到,唯有在強制性別分化的文化中,閹割情結才成為成長過程中不可逃避的階段。其他女性主義者,如哈定(Sandra Harding)、弗來斯(Jane Flax)等人也都有效地運用精神分析去探索男性文化特徵和解構男性氣質。
劉毓秀先從佛洛伊德對性與性別的分析著手,引入拉岡的語言分析、鏡像期理論、象徵秩序等概念,接著介紹丁尼思坦等人在佛氏理論基礎上對幼兒人格養成的詮釋,以及其他女性主義者,如布倫南(Teresa Brennan 1952-2003)等如何在精神分析的基礎上,試圖創造陰陽均衡的文化。
當代社會主義女性主義
在二十世紀,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受到激進派和其他流派影響,發現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分析完全忽略了主要由女性無償承擔的再生產勞務,因此特別注重再生產自由、家務勞動、家庭工資等課題,採用歷史唯物論來探討女性受壓迫的原因,也將階級觀念帶入性別體系分析。法國女性主義者戴菲(Christine Delphy)認為,許多女人錯誤歸類自己的階級屬性,不是認同父親就是認同丈夫,以致性別壓迫附屬於階級壓迫之下,戴菲主張女性自成一階級,她們的共同特性是都被依丈夫的階級分類。
在第六章中,范情介紹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發展初期,用以分析資本主義和父權體制的雙系統理論及統合系統理論,前者以米契爾和哈特曼(Heidi Hartmann)為代表,基本上認為資本主義和父權為兩套分別運作於公、私領域的社會關係,各自代表不同利益,二者互相結合,推助不同階級的男人團結,共同掌控女人的勞動力。因此需要分別分析資本主義和父權體制,以及二者的辯證關係,以便破解婦女受壓迫的原因。然而資本主義和父權體制並非兩套互相絕緣的系統,公領域的權威更時時介入私領域,當女性勞工不只是以女人或勞工,而是以女性勞工的身分被壓迫時,雙系統理論就顯得捉襟見肘。統合系統理論則以楊(Iris Young)和潔格(Alison Jagger)為代表,她們整合資本主義和父權為一個統合的概念來分析婦女的處境,以女性主義的歷史唯物論,補充馬克斯分析中的性別盲點。楊的性別分工分析、傑格的異化和再生產理論都為馬克斯主義注入新的、女性的觀點。
社會主義女性主義不只追求新的、平等的社會制度,更要根本改變人的意識結構和本能需求,使人的本能由宰制和剝削的慾求中解脫出來,不只利用生產力削減異化勞動和勞動時間,並且以生命本身為目標,使知性和感性都得到充分開發,讓人類能夠享用自己的「生存」。在人的勞動力逐漸由資訊科技取代的此刻,如何生存已經成為不容忽視的新課題。新馬學者馬庫色(Herbert Marcusea)將婦女解放運動視為當前最重要的社會運動,他並且預測,婦解具有演化成相當徹底的政治運動的潛力。
女同志理論
女同志運動可說是激進女性主義中最激進的部分,對女同志而言,對女人產生情慾已不只是性偏好,也是自覺的、政治的選擇,用以徹底挑戰異性戀體制的「正常性」和異性戀關係中的男性主控權。女同志以女人愛女人、女人認同女人的行動來擺脫男人的控制和定義,不再以男人為中心,也以女同志理論激發人們對性與性別、自然與文化的重新思考。詩人芮曲(Andrienne Rich 1929-2012)提出「女同志連續體」(lesbian continuum)的概念,所有認同女人的女人都可以是女同志,不受限於性慾取向。詩人羅得(Audre Lorde)則以黑人女性的經驗揭露婦運陣營內差異政治之存在,表面和諧下潛藏的排擠與漠視。她以「情慾小黃球」比喻女人自主的情慾(the erotic),蘊含性愛、生理、情感、心靈與智識的內在生命能量與創造力;和男人定義的色情(the pornographic),將一切化約為性交與感官刺激,而無情感與力量可言,有著雲泥之別。法國小說家和理論家維蒂格(Monique Wittig
1935-2003)主張,所有生理分類都是社會建構的成果,是壓迫機制創造了生理性別,而非生理性別創造了壓迫機制,一切性別差異都是異性戀思維的產物,為了突破異性戀機制的壟斷,她喊出「女同志非女人」的口號。魯冰(Gayle Rubin)為情慾少數發言,批判異性戀霸權的性階層化,女性主義是性別壓迫的理論,不適用於處理性慾議題。巴特勒(Judith
Butler)以女同志的身分反對「自然化」性慾取向,也反對將之化約為性別,主張「反認同、反性別的性慾取向」(sexuality against identity, against gender),提出「性別操演」(gender performativity)理論,指稱性別是異性戀機制下強制而又強迫的重覆,不僅由社會建構,也並不穩定。
在本章中,張小虹和鄭美里充分剖析了女同志與女同性戀之差異、社會性別與性慾取向的差異、本質論與建構論之爭、重要理論家的主張以及臺灣的女同志運動。
生態女性主義
生態女性主義雖是一種古老的生活態度和實踐,卻是七○年代嶄新的名詞和社會運動,源起於全球各地婦女自主性的行動,有時被稱為第三波婦運。生態女性主義在理論上總結各流派女性主義對人與人、人與自然之間宰制與附庸關係的檢討。魯瑟(Rosemary Ruether)指出,西方意識型態將女人、身體與自然並列,並且強調文化超越身體及自然而具有優越性,使得男人對女人和自然的壓迫變得理所當然。丁尼思坦認為,人類嬰兒期形成的對母親(代表和控制所需的一切資源)的依賴,使我們對自然和女性都一方面欲占有和搾取,另一方面卻渴求和解與補償。女人也因為認同母親其兼具非人和超人的屬性,而接受這樣的命運。墨欽(Carolyn Merchant)追溯前現代人們視宇宙為一活生生的有機體及滋養的母親,對之懷有崇敬和不忍加害之心。科學革命後,宇宙成了機械性的存在,不再具有人性或精神力量,以致於由(男)人宰制。
對於啟蒙運動以後歐洲的男權至上和人類中心思想,生態女性主義者提出批判,抗議其產製的生態災難,以各種具體行動(包括護樹、吃素)防止環境破壞和動物虐殺,追求世界萬物的永續共存。自然生態女性主義認為,女人本質上與自然親密,養育、關懷和直覺是女人的正面特質,應發揚女人與自然的聯繫,否認男性與文化的優越性,堅持自然與女性是和文化與男性相平等。更多生態女性主義者主張,女人和自然的關係是社會建構的結果,因此是可以改變的。在策略上,她們反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模式與商品邏輯,主張整合生產與消費,以達到去工業化和去商品化的目標。她們強調身體力行和社區改造的重要,不僅在行動上實踐生活環保和參與式民主,也堅持以行動來體現其價值觀:互助、關愛、非暴力、非競爭、普遍性參與、整體性思考等。她們的保育觀點雖與深度生態學 ( deep ecology)有許多交集,但是對主流的生態保育運動仍保留不同立場,對其中的男性中心思想和性別歧視不予苟同,她們主張個人和政治層面的權力濫用才導致人際壓迫和環境受創,必須從個人和集體兩方面雙管齊下,加以改造,才能挽救人類和萬物共生的地球免於毀滅。
後現代女性主義
「後現代」本身是一個模糊的概念,「後現代主義」挑戰所有的權威、真相和表象,追求去中心化,肯定多元和差異,因而後現代女性主義本身的定義也十分多元與分歧。三位採用法文寫作的女性作家西蘇(Hélène Cixous)、伊希迦赫(Luce
Irigaray)及克瑞絲緹娃(Julia Kristeva)企圖解構以陽性價值為主導的社會/政治倫理,鬆動僵固的二分法思考模式,以多元、開放、包容差異的理念為女性的壓迫尋求解答和出路,三人的共同點在反轉女性的第二性劣勢處境,利用其邊緣、流動的位置做為反抗的據點,挑戰父權。她們的著作在美國學界受到歡迎,被稱為法國女性主義,也被視為後現代女性主義的代表。不過選擇「代表」之舉就相當非「後現代」,而三人本身也未必承認自己是女性主義者。法國著名的女性主義者波娃和戴菲便因為三人強調性別差異、肯定女性特質,而指她們的理念更接近本質論,而非女性主義。
西蘇提出陰性書寫的主張,女人透過書寫傳達自己的認知和經驗,突破父權崇拜陽具、定於一尊的框架,回歸充滿生機、無限寬廣的母性。她認為父權文化中所謂的雙性,只是徒具陰陽同體的外表,抹煞了女性異質,只有女人才是真正雙性的,以「另一種雙性」彰顯女性特具的多重主體。
伊希迦赫反駁佛洛伊德的陽具歆羨理論,認為此論調暴露了男性的惶恐,他們無法忍受女人在心態上根本無意擁有陽具。她主張男女的身體構造不同,性愛需求也不同,男人必須藉他者獲取滿足,女人則可以產生自體快感。她希望女性多方面發揮潛能,展現其如流水的豐沛能量,在彼此互為主體的互動中捍衛母系族譜,拒絕臣服於男性。近年她推廣瑜伽,整合身心靈,一方面維護個人主體性,同時與他者保持對等與互相傾聽的和諧關係。
克瑞絲緹娃則是否定女性這個概念,也反對陰性書寫之將女性本質化,她將主體看成持續不絕的醞釀狀態,解構主體認同。不過她肯定母性,認為懷孕和養育可以使女性獲得愉悅,打破人我界線,消弭主體對客體的壓迫。
在第九章中莊子秀對三位的論述有相當深入而完整的介紹,也納入其他女性主義者對她們的批判以及辯護。
國家女性主義
各流派女性主義都不忘分析女性在父權的國和家之內的處境,從質疑父權、夫權開始,解析國家體制的父權本質。激進和生態女性主義者對於國家、政府或政黨的龐大組織存有疑慮,不僅本身偏向於採取獨立、分治的組織型態,也與政府和政黨保持距離。自十九世紀起,自由主義女性主義即選擇了在現有體制(包括各國政府及國際組織,如國際聯盟和聯合國)內改革的路徑,積極爭取與男性並肩參與政治運作。在現實情境中,北歐的國家女性主義指體制內女性主義者和體制外婦運者合作,建構對女性友善的福利國家的過程;前共產國家則泛指男性黨國領導者所制定的婦女政策;當下最廣泛認定的,當屬聯合國推動各國政府建立機制以提升婦女政經地位的種種措施。其最受矚目的手段包括:保障名額或性別比例制、婦女/性別政策機構、性別主流化,三者都是由上而下的變革,與由下而上的草根婦運相輔相成。
為了實現男女平等參與決策,性別比例制是提升婦女人數最快的方法。我國首先於一九四六年以憲法保障女性民意代表當選名額,二〇〇八年立法委員選舉首採比例代表制,各政黨不分區立委當選名單中,婦女不得低於二分之一。一九八〇年代,瑞典、荷蘭等國採行政黨提名性別比例制(party quotas),政黨在提名階段自動提升女性候選人的比例。一九九〇年代後,南美和亞非國家大量採用增加法定當選人數的性別比例制(legal quotas),以三分之一為原則。仰仗性別身分當選的女性,並沒有法律義務為女性代言,或對女性群體負責,但仍被期望能夠為民意機關帶入女性視野,淡化公私領域的傳統界線。女性人數突增也可能對組織文化造成「性別衝擊」(gender shock),改變民意機關的政治體質。
一九七五年第一屆世婦會後,各國設立婦女政策機構,聚焦於女性議題,機構內的女性主義官員結合了女性民意代表與婦女運動,形成了內外並進、提升婦女地位的鐵三角,一方面從外部挑戰性別階層化,同時在政府內部進行改造。臺灣的婦女政策機構起步晚,但發展快速且權力獨大,一九九七年行政院成立婦權會,二〇〇〇年發展成「行政權力中心」,民間委員權力大過正式文官,成為政府重要決策者。
一九九五年北京世婦會之後,「性別主流化」成為聯合國的指導性政策,要求各國政府將性別觀點納入所有政策和方案,在做決策前需分析對女男各有何影響。只是性別主流化意義模糊,因而各國各自解釋,各設目標。有些國家以主流化為手段,將性別平等推廣至政府各部門,提升女性地位;也有的趁機強調性別包括男女,而撤消了原有的婦權機制,反而削弱了女性立場;也有歐盟國家為爭取補助而機械化執行歐盟指定的性別主流化政策工具,並無實質效益。臺灣於二〇〇三年引入性別主流化,除了推進體制內婦運,也趁機創造出「多元性別」,一併帶入同志運動。「性別平等」一詞使用廣泛,但其定義和內容卻鮮少經過民主、公開的討論,以致不同立場各自表述,成為權力角力的新場域,卻少了平等,也成就了新的權威。
後殖民女性主義/第三世界女性主義
女性主義產生於西方白人中產階級的文化脈絡,難免有種族、階級、文化和時代的盲點,自一九八〇年代起受到非白人和曾經殖民統治的英語系國家的女性主義者批判,指其為西方、白人經驗中心的帝國主義女性主義,不僅將婦女視為一元化之群體,忽略了第三世界被殖民的歷史處境,以及女性之間不同的政經利益,也無視前殖民時期第三世界國家中已存在的男女平等思想,將第三世界婦女視為純粹的受害者,不具任何反抗精神,而且過分強調性別和性慾。她們認為對第三世界婦女而言,女性主義以性別抗爭為焦點的做法過於窄化,爭取男女平等應同時反對種族歧視、經濟壓迫和軍事侵略,方能達到全球女性的真正解放。
黑人女性主義者柯林斯(Patricia
Hill Collins)以黑人女性經驗為核心,對照主流文化論述的歐洲中心主義及陽剛思維。她指出黑人女性同時承受種族、性別與階級的多重壓迫,多重壓迫的概念有助延伸思考不同身份的女性如何同時受制於資本主義、父權主義、種族歧視或異性戀中心主義。壓迫不只是存在於結構的層次,也可從意識、文化脈絡及社會組織層次進行分析。個人可能同時是壓迫者、也是被壓迫者。後殖民女性主義另一重要概念為交織性(Intersectionality),黑人女性像是站在交叉路口,同時受到多重壓迫碾壓,需要同時處理。
西方國家常以其文化優越感拯救覆蓋面紗的伊斯蘭女人,或行割禮的非洲女人,並以此做為軍事侵略外國的藉口。第三世界女人並不像西方所想像的,是單一且同質的團體,即使在同一國家中,亦有社經地位、宗教信仰之異,需要同時具有文化意義與社會歷史的性別分析。史碧華克(Gayatri C. Spivak)尤其關注「土著女性」的主體性,以及她們如何被消音。莫寒娣(Chandra Mohanty)主張,第三世界女性主義者不應以共同的膚色、性別出發,而是應當基於對種族、階級和性別的共同思考方式,建立政治合作共同體,做為反抗強權的基地。芮曲則提出定位政治(politics
of location),提醒個人自省其受到種族、階級影響的性別想像,並且允許他者在其特定政治、地理位置上發言。
在本書最後一章,林津如詳敘二十世紀晚期後,受女性主義洗禮的非西方非白人女性對女性主義的回應與批判、女性主義者的自省,西方強權如何以拯救女性之名行帝國主義侵略之實,以及第三世界女性主義者如何發掘邊緣個體的自主性,跨國合作,聯合抵抗。
一百多年以來,從西方、白人、中產女性省思自我處境開始,女性主義理論不斷演變、擴散,探討如何以女性經驗來改造充斥暴力、歧視和偏見的父權體系,衍生出多元視角和性別、階級、經濟、文化、政治的多重分析。改造父權是一個遙遠的目標,但女性主義的批判和反省精神已使我們愈來愈能明辨各種差異和壓迫,並且學習尊重不同文化、社會脈絡下的個人,以互為主體的方式互相對待,擺脫優勢者的俯視姿態,克制將自己的價值強加在他者身上,開啟更多坦然、互相傾聽的對話。
[1]日本著名的女性主義學者上野千鶴子在其著作《厭女:日本的女性嫌惡》(2015:34,聯合文學中譯本)中,這樣說明厭女症:男人否認女人是等同於自己的性主體,並且把女人客體化和他者化,這種蔑視女性的表現即可稱為厭女症。也就是說患者認為男人才是人,才有主體性,女人是附屬的丶次要的存在,他/她總是用男性的眼光或利益來評價丶眨抑女人。在由男權主導的社會,女人也可能內化男性價值而崇拜男人丶輕視自己,也患有厭女症。
加註: Radical feminism最初被翻譯成激進女性主義,也廣為採用。1990年代傳大為主張改為基進女性主義,理由是radical 的字根是root,根的意思,基有根本之意,基進意謂根本改造,所以有些人開始用基進取代激進。但是基也有基本之意,貼近fundamentalist,基本教義派,radical feminism的批判和革命精神卻是與fundamentalism的嚴守基本教條大異其趣的。基進是一個新詞,許多讀者感到陌生或不解,認為這是一個學術性的名詞。
激進則是大眾熟悉的中文,激是指水流而下,遇到阻力,而水花飛濺、震蕩,有急劇、猛烈之意,所以激進有激烈、激情的意象,貼切描繪了1970年代青春女性發展出的婦女解放運動和激進女性主義。激進也意謂徹底而激烈的改變,有人從策略的角度認為這與我們傳統中庸之道不符,易引發反感,而不宜採用。但是激進女性主義的確因為挑戰父權成規而備受攻擊打壓,許多前輩為此付出了極大的代價,我們更不該為了降低抗拒而改名換姓吧?
《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舊版採用基進女性主義,之後我自己常以激進/基進二者並列,本書改寫後的《女性主義理論與流變》在文字上力求明白易懂,也希望女性主義得到更多人接受,所以全書使用激進女性主義,不再基進。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